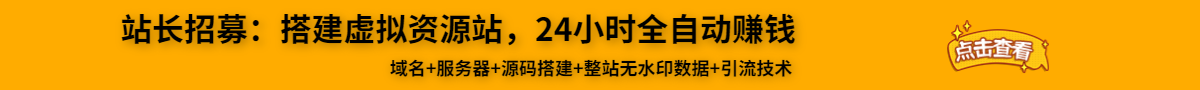原创白屋
本文来自公众号白巔疯

1
二十二岁那年,我被省城甩出去三百多公里。
其实说甩出去是不对的,我只不过是滚回了老家去。你可别小瞧这三百多公里,过去的老解放大轿子,一路爬山过梁,要走10个小时以上。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,火车还没有开通,高速公路更是枉谈,只能一任这老铁牛载着,颠簸摇荡,喘叹咳急。
四年的省城生活,给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面窗户,让我读了许多书,知道了许多人,了解了更为丰富的世界,并且变得凌虚飘渺不切实际。读过了《人生》,就知道了有一个叫高加林的人。我的命运其实与高加林差不了多少,比他幸运的是,我如愿地成了一个城里人。和他一样的是,我依然还属于我自己脚下的这片黄土地。
分配,是一件美妙的事,从此让你有了工作,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薪水。从此让你摆脱了对家长的依赖,成了一个独立的人。
可分配,也把本是一个教室甚至是一个宿舍培养出来的人,从此天涯两隔。有的人进了京,有的人留了校,有的人却要被派遣到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。分配,是人生命运的分界点,从此便有了天堂和地狱。
尽管到了后来,有人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,通过各种渠道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,但大多数人,都成了分配制度下屈从的奴隶。
回顾我人生走过的30多年的里程,站在一个相对的终点看起点,我发现我其实还算是一个顽强的人,一个勇于与命运相抗争的人,一个将作家梦进行到底的人。
2
我是怀揣着写作的梦进入大学的。
高中时,因为一篇作文,我变得膨胀无比。
开过一场运动会后,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是《运动场记事》。在那个没有青春期的年代里,我却极早地进入到了逆反期。
不愿意按照老师布置的题目写,于是自作主张写了篇抒情散文《运动场赞》。这样的行为若是放在当下,肯定算脱题,肯定是要给零分的。可令我想不到的是,老师竟然把这样一篇不按要求作的文章,刻成蜡版,当成优秀作文讲评。
彼时正逢地区教研室的人来听课,而我的那篇作文,又被人拿出去发表在了当地的教育研究的刊物上。后来出版过的一本作文精选,则又被选了进去。
我的语文老师,名叫寇炳武,曾被打成右派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多年的春秋。那时没有语文教材,他上课讲的内容,都是即兴发挥。
有一天他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,说你要给咱好好写。写作这事,基本是天生的,这个班就看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了。别看某人也立志想当个作家,他没戏。
我惴惴地从他的办公室出来,心里便有了种莫名的兴奋。
等高考报志愿的时候,毫不犹豫,所有的专业都填报了中文系。
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傻,根本不知道中文系其实培养出来的作家是很少的,根本不知道,其他专业也能出作家的。
后来反思,为什么中文系里出的作家少?主要是理论学的太多了。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其实是南辕北辙的。一个以形象取胜,一个以说理为据;一个用的是感性思维,一个用的是理性思维。理论学得过好的人,写作议论文还可以,写小说基本是不着调的。
寇炳武老师,自打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。他之今天尚在人间否,也已不知道了。但他留给我的这句话,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后来我自己也做了老师,我之影响过几个人,扪心而问,总感觉很是慌愧。
3
我的逆反期,相对要长很多。上了大学之后,就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,一路被歧视和打压着。甚至到了老年,似乎这种叛逆还未完全过去。
港衫、喇叭裤、长头发,似乎是那一时期叛逆青年的标配。
我的叛逆还有一个标志,就是写朦胧诗。
我看不上那些激情澎湃的朗诵诗,看不上那些软塌塌的抒情诗,感觉诗只有朦胧、高渺、凌虚,才是当时最合适的表达。
可是,自打朦胧诗一出现,就遭到了许多名人专家的打压。
反对最激烈的,当属公刘。最后艾青也站出来,对于这种大家似乎都看不懂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最后一击。朦胧诗,就这样被腰斩了。
记得在西安市一中实习的时候,我上街买了本《诗探索》,上面选了顾城的几首诗。我把其中一首《安慰》,读给所有的同学听。那时我们19个男生,住在一间大教室里。听了我的朗读之后,有个同学就说,这TM的就是狗屁。我感觉我与顾城的心灵是相通的,对于《安慰》一诗,我也有自己的理解。直到今天,我还会偶尔将它写在黑板上,讲给我的学生听。
那个时候要成为一个诗人,必须是要发表的。我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诗,想发表是根本没门的。加上分配被贬回了老家,信息隔敝,形孤影单,写诗的欲望就此便消沉了下去。
最终,我的诗人梦就这样破灭了。
4
80年代末期,我名下来了两个延大实习生,其中一个叫韩万胜,榆林神木人,一只手永远插在裤兜里,据说手有残疾。
这个年轻人很厉害,大学期间就发表过许多诗和散文。这让我这个消沉又颓丧的同样有着作家梦的人,对他很是佩服。
他说,诗你就别写了,改写散文吧。散文更能顺畅地表达自己。我给你介绍一个作家,即《延安报》的杨葆铭先生。
彼时的延安,有一份刊物一份报纸,报纸叫《延安报》,后来改成日报了。
于是,我们就一人骑一辆自行车,跑到凤凰山麓下的杨葆铭先生的家,拜见了他。葆铭兄在凤凰山的住处,背靠山的两孔窑洞,是他的住所,他自己则在窑洞前盖了两间平板房,于此读书写作。
葆铭兄长我六岁,高个,白净面皮,善谈,个人修养极高,且没有架子,时任《延安报》政文部主任。他编的版块里,有个栏目文艺副刊叫《杨家岭》。于是我就抹了些文字,发表在那上面。
我向来对于有架子的人,内心是极排斥的,并认为那是自卑的表现。因为与葆铭兄有共同语言,所以就经常黑更半夜的,骑车去他家闲聊。有些以为好的文章,就投给他发表出来。时间久了,我就积攒出了一沓手稿,有发表的,有没发的,结在一起出了个散文集,取名叫《黄土人语》。那一年,我30岁。
这些年来,我一直保持着与葆铭兄的往来,一直尊敬他为老哥,也一直想给他写篇文章,但总也感觉自己拿捏不准,总想着再沉淀一下。这倒不是因为他帮我走出困境,帮我成了一个真正写作的人,而是打心底里的钦敬。
5
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了,集子也结了,我是不是就成了一个作家了呢?
答案是否定的。我感觉自己离作家这个行当,反而越来越远了。
多年来我始终认为,作家是一种边缘化的职业,作家要离体制越远越好。
一个真正的作家,必须要对人生、社会、灵魂作终极追问,要对于当下的背面作深刻反思,尤其是在一个不健全、不周正的时代。真的作家是不随大流不入主流的。
从这一意义来看,我得感谢我所学的文学专业。它让我阅检了无数高贵人的思想艾青十首最著名的诗,让我与远近的许许多多的伟大心灵沟通过,我在写作的道路上,成了一个在灵魂上有追求的人。
所以,在以后的时光里,虽然有机会进入到行政部门去,虽然可能会成为一个官员,我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
此所谓成也文学,败也文学。
就人生的富贵荣华来讲,成为一名官员可能要好得多。但我知道,陶渊明与李白对我的影响很深,我弯不下自己这高贵的腰。
我一如既往地坚守着我伟大的写作梦想。
但我不是作家。我没有加入过任何作协。尽管老家的作协,据说还分给了我一个小头目的官职,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。
6
2015年,我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梦想着留居的省城里,移住到我神往的终南山。
站在山巅,我立刻有了一种神一般的感觉,似乎在这里,可以藐视一切滚滚红尘了。我神经质地认为,我已经不属于眼前这个热闹的社会,我只是站在社会的边上。
2016年年底,开始写公众号文章。
四年多的时间里,工作上课之余,竟然累积出了500余篇心血之作。有朋友劝说,可以再出个集子了。我明确地告诉他们,如果在没有文字审查的情况下,我是愿意出集子的。若不能,我是宁可不出的。写文章无非是想说自己心里的话,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出它又有何意思呢?
有的人出的集子很多,我却从心里瞧不上他。作家只是许多人头上的光环,并不能说明他真有写作能力的。假如有人脉,卖点钱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许多所谓作家,不过是人类精神的垃圾制造者艾青十首最著名的诗,还费掉了许多木材纸浆。
我宁可让自己的这些文字自生自灭,让它成为网络垃圾。
这些年里,我写的理论书已经够多,至于作品集,不出也就罢了。
也许在体制作家看来,网络写手就不是个作家。
但即使你印成了书,又有几个人读呢?没有人读的书当然也叫书,可没人看的作家还是个作家么?
即使网络写作,有的人动辄10万加,有的人却只有几百阅读量,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阅读者的水平,从朦胧诗时代就让我明白了这人间况味的。
写作,无非是慰藉自己的灵魂,同时找到三观一致者,而已。
我自己知道,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,但我怀揣着写作的梦想。
7
前几日的清明节,应石岗兄盛邀,我去了趟礼泉县,拜见了心仪已久的阎纲先生。
这位年届90的智者,这位有风骨的老人,这位现当代文学的见证者,在他人生的晚年,却依然坚守着灵魂的高地。他的这一生,也许并没有写出太令人激动的文章,但他的良知,他的人格魅力,却让我五体着地了。在我心中,他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。
晚上住在石岗家,和他一起吹大牛。石岗兄大我三天,却是我的师弟,虽然认识他的时间很晚,却似乎灵魂早就碰撞到一起了。他经历广,见得人多,是个难得的明白人。
这一夜,石岗兄将我的三观给彻底颠覆了。
在石岗兄看来,文学已经死亡了。人们的阅读会转向视频与娱乐,没有人再读文学作品了。未来社会只有三个东西影响着人类的生活,一是资本、二是科技、三是娱乐。未来的作家也必然是多方面的,不是只写文学作品的人才被称为作家。
其实我心里也知道,文学已经差不多死亡了,虽然现在只是气息奄奄。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,文学作品还是有人读的,虽然它变成了小众文化。我顽固地认为,阅读在未来社会会分出层次来,高层次的人,一定还会读文学作品的。近闻余华的新作《文城》,首印就是60万册,而且瞬间卖光,这足以说明阅读文学作品还是一种大众日常的文化生活。
礼泉一夜,让我心目中的文学神圣性,彻底被石岗兄肢解掉了。
回到终南,我甚至不想再写一个字。无精打采,精力不济,我把这种情况对友人戏称是大姨父来了。
写作如果没有人读,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?
社会越是向前发展,神圣越是被后人解构。
过去有着皇权象征的鼎,有谁现在还会用它来煮肉呢?
仓颉造字时,天雨粟,神鬼哭,人类之于文字的敬畏,现在哪里还有哪怕是一丁点呢?
唐诗在宋代变成了词,在元代变成了曲,在明清开始流行成小说。一代解构一代的神圣,这神圣到现在又被短视频和抖音给彻底瓦解了。
这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贵族,面对新兴资本主义,他们已经很穷了,但即使吃不上饭,也要给地板打蜡,也要摆上银烛台,以显示自己贵族的身份。
这还让我想起了孔乙己,即使再穷困,也不能脱下象征了知识人身份的长袍。
但我也并未完全灰心,无论社会怎么发展,无论神圣怎么转移,人类社会永恒的那块不可侵犯的宝地,却一定会在的。文学的样式可以变化,亘古不移的,是它的精神内核。我相信等这尘埃涤尽,浮华过后,人类还会有相当多的人,走到这块灵魂的高地上来,凝视人类精神的家园。
想到这里,我就又一次执起键盘,敲打出了以上的这些文字。
但于心里,我还是不断发问,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人,还是个作家么?
正如我的那个同学所言,狗屁都不是。
谁再叫我作家,就是在骂我。呵呵。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9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kkf7008